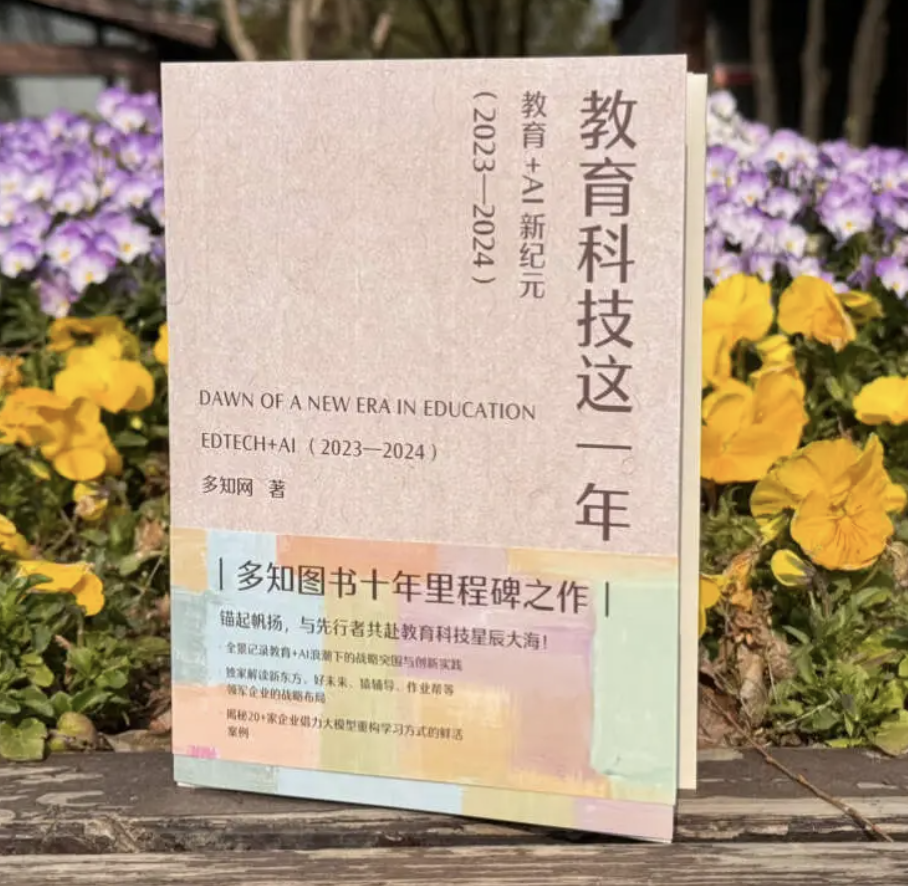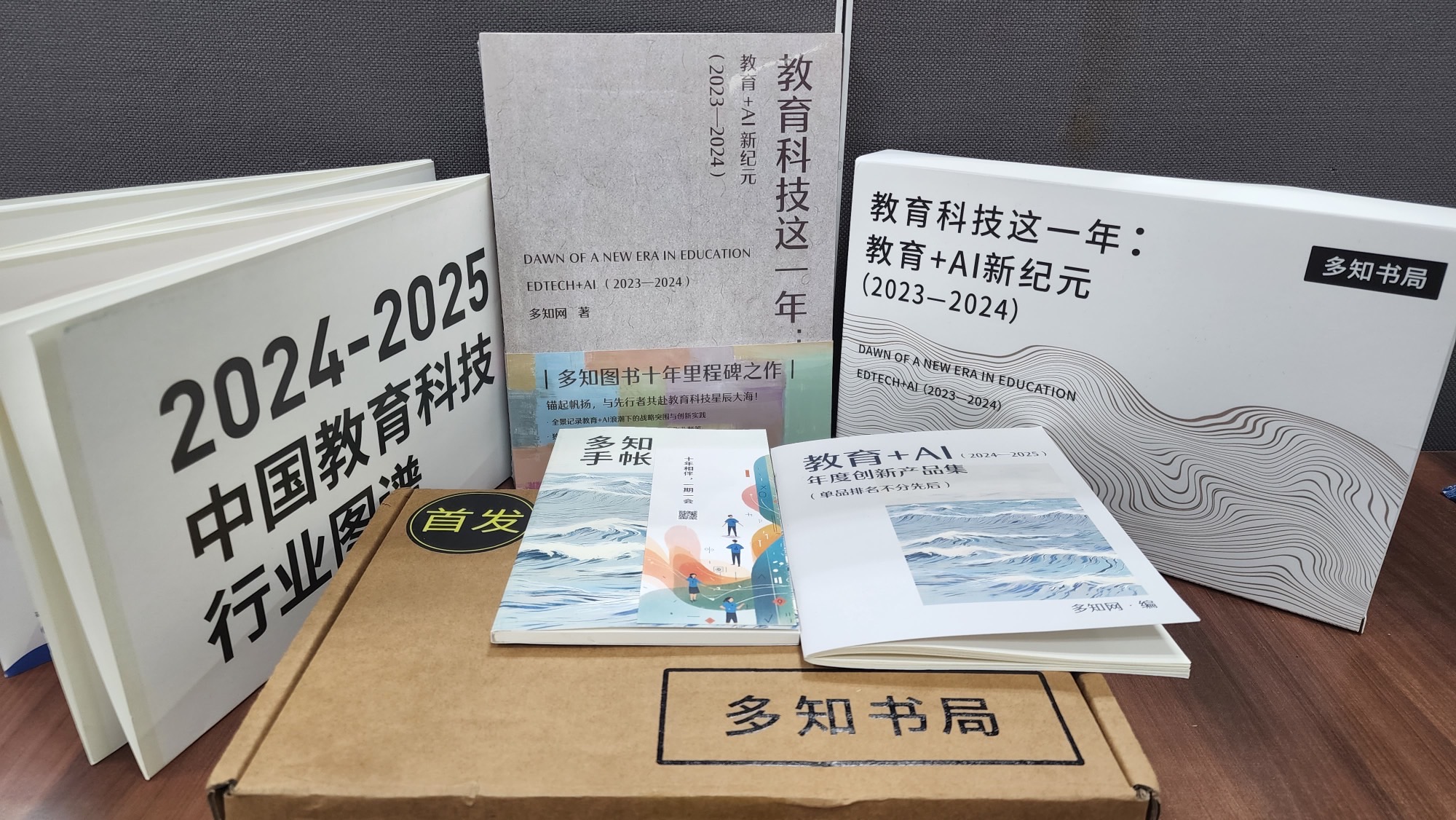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:我们的孩子有能力改变世界,可我们常常只要他们“听话”
编者按:
本文转载自“外滩教育”。西湖大学校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认为,要培养创新人才,教育者首先必须放下对“乖孩子”的执念,鼓励他们独立思考、敢于质疑,拥抱更大的理想。
来源|外滩教育(ID:TBEducation)
作者|张楠
编辑|Iris
图片|西湖大学
周六早晨,施一公匆匆上线,出现在屏幕上。他刚刚送走一位因为选课苦恼来咨询的本科生,下午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讲座要参加......每一天,都被日程表以小时为单位分割开来,是施一公如今的日常。
言语坦率,开诚布公,谈问题直指核心,简单的开场问好后,外滩君立即感受到他十足科学家的风格。
施一公
作为颇受公众关注的顶尖科学家,施一公自有他的学术成就和个人魅力,但更令人想要一探究竟的,还有他一次次做出的那些跨度颇大、挑战也不小的抉择——
少时保送清华、后赴美读博,2001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;
2008年放弃美国终身教职,回到母校清华任教,在清华十年,先后担任了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、清华大学副校长;
2018年,辞去清华职务,从零开始创办西湖大学。
结构生物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施一公,从此多了一个身份,“西湖大学校长”。尽管西湖大学内部的老师学生们,更愿意简单、亲切地称他“施老师”。
今年4月,施一公的首部作品《自我突围》出版,书中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、求学、科研经历,以及他对教育、人才、科研体制问题的思考。对于近些年全身心投入在建设西湖大学的施一公来说,这算是一次罕见的“高调”。
施一公新书《自我突围:向理想前行》
图源 中信出版社
新书分享会上,他站在台上讲,选择这时候出书,一是看到网络上许多碎片化的、被曲解的“施一公说”,他想,不如自己来说,让素昧平生的人们看见一个更真实的施一公;二来则是出于感恩,记述下曾对他产生重大人生影响的人和事。
最后一点小私心,还是希望能借助这本书,让更多人关注到西湖大学,让更多人能和他一起来干这件“大事”。
他把这里视作余生理想的“终极凝练”,直言要把它建设成“世界顶尖大学”,培养一批有理想、敢担当的年轻人,成为中国科研乃至世界科研的重要力量。
作为顶尖科学家,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到了哪些反思?西湖大学成立后的第5个年头,在培养科技创新人才这件事上,他有怎样独到的见解?
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,
如何自我突围?
父亲给他取名“一公”,寓意“一心为公”。而这也成了对施一公影响最大的一句话。
施一公出生于河南郑州,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驻马店小郭庄。1977年恢复高考时,施一公读小学四年级,还懵懵懂懂地、好奇父亲为什么要那么上心。看着父亲每天都很投入地给大姐、表哥和表姐辅导功课,讲方程式、讲热力学,感觉很酷、很神秘。
受哥哥姐姐们高考的影响,施一公也渐渐向往起那些更高深的数学、物理知识。
这一年,他开始自学五年级的功课,两年后小升初,直接考到了全镇第一名......1985年,因前一年在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河南赛区获得第一名,他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。
1988年,施一公(左二)与大学同学白林(左一)、俞新天(右二)、包绍文(右一)在清华学堂前合影
被施一公视为偶像的父亲,幽默、豪爽,待人宽厚,但于他,却是一位既慈祥又严格的父亲,很少批评,也很少表扬,总是希望他能做得再好一点儿。而施一公自己,也很是努力进取、希望成为父亲的骄傲。
同样对他寄予厚望的,还有看着他一路走来的老师、同学。高中的毕业册上,还有位同班同学留言说,“希望能成为未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少年时的同窗。”
备受鼓舞的施一公,一直朝着科学的顶峰奋力前行。提前一年从清华本科毕业后,他先是在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、随后在斯隆-凯特琳癌症研究所(MSKCC)做博士后。1997年,又顺利拿到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的教职。
1998至2002的5年间,施一公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科学界三大顶级期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,在其研究领域内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誉。
施一公在实验室
治学之路一路顺遂,但国内外的求学经历,却让习惯边前进边思考的施一公感到一丝怅然,甚至开始反思自己攻读博士最初的心态和思路——
应试教育下养成的解题思维,让他主动选择有稳定预期和回报丰厚的科研课题,潜意识回避了高风险的基础前沿课题。然而,科学研究的最前沿的一些重大突破,往往来自那些前途不明的、高风险的课题领域。
基于这样的经历,施一公讲自己,既是应试教育的产物,也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。但把时间拉长,他逐渐意识到:长期的应试教育影响下,从事科研最需要、最珍贵的原创精神,在他身上被束缚住了。
于是,2008年,当他全职回到清华后,他立刻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在科研上,施一公的实验室用很小一部分力量延续来自普林斯顿的课题,而把大部分力量用于挑战科研的无人之地。
这并非易事。正如施一公当年经历过的迷惘一样,年轻人刚开始选择课题时,都不够自信、害怕失败,急于“求成”。再加上,好几年的研究得不到实质进展,其他延续保守课题的同学却能不停地发论文,横向一对比,学生们自然更焦虑、挣扎。
施一公和学生
作为跟学生们并肩奋战的导师,施一公也不是没有动摇过,但一想到要重回循规蹈矩的老路,他还是决定,要再坚持一下。“创新就是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,要突破,就只能勇往直前地探索。”
一边硬着头皮给团队打气,一边调整策略、集中力量逐个击破。终于,自2013年起,实验室期待已久的突破性进展,开始陆续出现。
在清华的试点成功,让施一公在办学校这件事上,更坚定了最初的想法:只有培养出一批真正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学生,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实现重大理论突破或核心技术攻关,才能真正提升一个领域的发展水平、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。
培养创新人才,
要鼓励学生敢质疑
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,创办于2018年的西湖大学,寄托了太多人对更好教育的理想。早几年,西湖大学仅培养博士研究生。去年,西湖大学在浙江省内试点首招本科生,被视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。
西湖大学首届本科生
一心想带领年轻人探索创新的施一公,在谈及这群年轻人时,瞬间变成了“话痨”。
做科研不是好走的路,但第一批进入西湖大学的本科生,对此坚定的程度甚至超出施一公本人的预期。而施一公对他们更多强调的,是希望他们能在西湖大学“介于自由与包容的氛围”中,找到自己的平衡。
采访前,一位本科生因为选课多而感到有些吃力,来找施一公求助谈心——西湖大学独有的导师体系下,自入学起,每位本科生就会有一名博士生导师。施一公也带了两位本科生,这便是其中一位——不过,这种师生关系中,施一公更像一位父亲、或是家里的长辈,鼓励学生做好生活、心理的平衡,即便有一两门课暂时出现挂科也没关系。
施一公在西湖大学2022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致辞
在科研里真正“苦”过的施一公,当然看重学生的刻苦和努力,因为“这是成功的必要条件”。但他更看重的,还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。
他多次强调,要培养创新人才,教育首要的任务,便是鼓励学生敢于质疑、敢于发问。
或许,授课或进实验室,都不是目的,而是方式。他真正想探索的,还是一种因材施教的教育,一种让学生的个性和潜能被充分激发和展现的氛围。
1、敢于质疑的品质,需要被鼓励
前阵子,施一公到广州一所中学参加活动,听几位中学生分享自己做科研的经历和思考。
在对他们的发言进行评述的时候,有两位同学站起来重新解释,对专家们评论进行补充,甚至是反驳。点评时,施一公特别表扬了他们,“在这样的场合勇敢站起来,你们很了不起。”
活动结束后,其他分享者中的一位女生,就来到施一公面前,眼眶泛泪地说,“没想到,施老师您喜欢这样的‘刺儿头’学生。”
她还对施一公说,以前,自己也会这样,喜欢跟老师争论,可常常被批评,她就慢慢“学乖”了,成绩也提升了。
施一公并不觉得意外。带博士生这么多年,他也见过不少习惯了“听话”的学生。有时候即便是老师说错了、感觉到不对,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反思自己的问题,是不是自己没理解?不习惯去挑战老师,或者说所谓的“权威”。
所以,与其说是施一公偏爱“唱反调”的学生,倒不如说,是他希望通过表现偏爱的方式,鼓励教育看见个性、珍视个性。
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也好、敢于质疑的精神也好,到了17、18岁的年纪,虽说还是可以培养,但已经很有限。所以,他更多强调,教育,尤其是中小学的教育,不要磨平学生的棱角。
而这首先需要教育者能够用一些例子去“刺激”他们,让他们意识到,这是一个值得被鼓励的、好的品质。
2、鼓励学生敢质疑,首先要“破除迷信”
那么,如何培养这种敢于质疑的品质?
施一公讲,老师很重要。老师首先要自己打破“权威”的架子。敢把自己的短板暴露在学生面前,让学生感受到,老师是可以被挑战的、接受平等交流的。
“做老师的都希望学生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’。可是,只会听话的学生,怎么可能‘胜于蓝’?只允许学生听话的老师,怎么可能教出‘胜于蓝’的学生?”
施一公和学生在实验室
现在,在实验室里数学、物理基础好的学生面前,施一公已经有类似的感受。“一些数学公式、冷冻电镜的理论,我确实不记得了。那我就直说,我看这些已经很陌生了。”
老师并不见得方方面面都比学生强,让学生获得这样的心理暗示,也是破除“听话思维”的一种做法。
“如果现在让我们这些教授去考清华,还考得上吗?我估计不太行。但我们还在教学生,有道理吗?应该吗?当然!”
一方面,老师们已经在专业精深的方向做出了成就,另一方面,老师能够告诉学生,这条路就是需要他们“破除迷信”、走出自己的路来。
3、提出好问题的能力,需要长期积累
保护、鼓励都是手段,目的还是让学生能够主动提出自己的问题、表达自己的思考。因此,在西湖大学,无论课堂还是讲座活动,“还有问题吗”、“这个问题很好”是学生们听到最多的话。
可,学生能一开始就提出好问题吗?
对于这个问题,施一公冷静指出,指望大学生在科学研究上提出好问题,本身就有点“天方夜谭”。甚至许多读到博士二年级的学生,要提出一个好的课题,也并非易事,一定要基于一个强大的知识系统才行。
所以某种程度上说,我们一直讲,大家要学会提问题,实际上是一个机械的说法,提好问题,非常不容易。
施一公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,读博士期间,听报告很少提问题,总觉得自己问题很愚蠢,提出来别人就会笑话。但后来,他发现,无论一个问题多简单,当一个人提出来,一定会有一批人响应,其实也想到了,但是不敢问。
这个现象在施一公看来,很有意思。也正因如此,才更要鼓励学生提问题。不管什么问题,只有学生敢提问题,敢和老师交流,问题才能越来越深入、越来越精彩。
施一公还说,很多诺奖得主的科研成果,也不是因为一开始就提出了关键的好问题,而是在专业体系中摸索着,“歪打正着”地发现了好问题。
“就好比,我想去西湖看美景,慕名而去,结果在路上,发现西溪湿地也很美,然后在西溪湿地逛了三小时,拍到不少好照片。西湖的照片大家已经看了无数次了,但西溪湿地却是我发现的。而且不是一开始规划好的,是意外发现的。”
好奇心旺盛、问题多了,讨论深入了,学会门道了,才能真正一点一点推出好问题来。
西湖大学,
希望培养怎样的人才
拥有专业科研必备的思维能力与探索精神,同时,有理想、敢担当。这大概是施一公对西湖大学“第一批吃螃蟹的”年轻人比较切实的期望。
作为一名科学家,施一公的眼光一向放得远,看得透。他说:“考试也好,学习知识也好,最终目的都不是为了通过考试、上大学,而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”
#FormatImgID_13#
施一公给西湖大学学生的开学第一课
尽管,现在,这种人生价值的问题,中学生们还想得比较少,或者想一想就被现在的教育方式给压下去了,没法想。
在施一公看来,家长们常常觉得,上了大学,就是到了终点,“上了清华、北大,了不起了!”但其实,人生的马拉松才刚刚开始。
“年轻人自己更是了,即使会被说阿Q、嘲笑不切实际,也一定不要不敢想。理想不独属于某一个特殊群体,每一个人都可以有。”施一公说。
施一公曾经的博士生中,有从很普通的大学甚至中专一步步努力到他的实验室的。用今天的标准看,他们都是“输在起跑线上”的人,但如今,他们比许多“天之骄子”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为这些学生感动的同时,施一公也更有感触:一个人要有“后劲”、有“大出息”,不管是老师、家长,还是学生自己,心里就要有一根弦儿——拿到大学的入场券,对于将来实现理想是重要的关卡,但它的成败也并不能决定一切。
最重要的是,能持续发挥引领作用的理想,不能丢。
施一公告诉学生,理想甚至都不一定要实现,事实上可能就是永远不会实现。但它会是一个方向、一个灯塔,是觉得辛苦、疲惫的时候抬起头来就能看到的北斗七星。
这种听上去颇为浪漫的说法,其实,在教育中再朴素不过——目标感中最关键的那个“感”,不正是虽不能至、心向往之?
2022年4月,B站UP主“蜡笔和小勋”访谈了施一公。对话中,施一公澄清了网络上流传的“施一公鼓励读博科研,不鼓励工作赚钱”的观点。
他表示,西湖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发挥学生最大的潜力,他支持学生去多种领域尝试,前提是“从兴趣出发,而不只是以是否赚钱为驱动力”。
在西湖大学本科生不分专业的前两年,施一公也建议学生多去看、多去体验,不必急着锚定一个方向开始“卷”。最重要,要经过实践验证是自己真正想要的。
而目标一旦确定,那就要去寻找有效的方式方法去达成。心智承压能力强,碰到麻烦自己解决、自己调适、自己去面对挫折寻找解决方案。这对于一个人,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是最有启发的人生指导。